夜江斜月照孤愁
——张祜与他的镇江夜泊
作者:郑立广
在西津渡曾见证无数繁华过往的待渡亭边,伫立着一尊清瘦的男子塑像。他身着唐代宽袍,面容清雅,眉宇间凝着一抹淡淡的忧思,常引得游人驻足端详。直至读罢碑上所镌刻的那首耳熟能详的诗,人们方才恍然:原来这位便是一生布衣、命运多舛的诗人张祜。
张祜,字承吉,唐代诗人。其籍贯或云清河(今河北),或曰南阳(今河南),晚年隐居于镇江丹阳,以布衣终老。他终生未仕,长年漂泊,行迹遍布大江南北。其诗题材广阔,无论宫词、山水、题咏寺观,皆有清雅佳构。诗风纯熟工整,流转自然,平易近人,每于简淡中见深致。张祜晚年寓居丹阳,常往来于镇江与扬州之间。某日他意欲渡江前往扬州,抵达渡口时却见暮色四合,渡船停运,只得暂宿于码头旁的一座小客栈中。夜深人静,孤馆寒窗,面对长江夜景,心中寂寥渐起,辗转难眠之际,他研墨提笔,写就了这首《题金陵渡》:
《题金陵渡》
金陵津渡小山楼,一宿行人自可愁。
潮落夜江斜月里,两三星火是瓜洲。
诗中“金陵”并非指今日南京,唐代时“金陵渡”实为镇江渡口之名。镇江古来便是南北水运要冲,踞守长江南岸,舟楫穿梭,行旅不绝。而诗末所提“瓜洲”,则位于江北,与镇江一水相隔,遥遥相望。夜色苍茫中,诗人独倚小楼,远眺对岸微茫闪烁的星火——那便是瓜洲了。
此诗前两句点出诗人夜宿之地,暗写孤寂心绪;后两句则以空灵笔法摹写金陵渡夜景,融情于景,映照出诗人深切的羁旅之愁。全篇以“愁”字为魂,融情于景,勾勒出潮落江寒、斜月低垂、星火微茫的江南夜景。笔致清丽淡远,意境幽深朦胧,于宁静凄迷的夜色中暗藏无尽思绪。全诗语言浅近而意境深远,结构严谨,余韵悠长,尽显张祜诗歌含蓄深婉、匠意天然的风格。
无独有偶,写作《题金陵渡》前后,张祜在夜宿镇江对面的瓜洲时,另一首《瓜洲闻晓角》,与之意境相通,同样清空高远:
《瓜洲闻晓角》
寒耿稀星照碧霄,月楼吹角夜江遥。
五更人起烟霜静,一曲残声遍落潮。
这首诗以清丽笔触,捕捉瓜洲拂晓时分的江景与角声。语言凝练,意象幽微,于静谧中渗出淡淡的旅愁,更借“残声随潮”之象,暗寓时光流转、万物更迭的深意。“五更人起烟霜静”既写清晨之宁谧,亦暗示新一日生活的开始;而“一曲残声遍落潮”则将听觉余响与视觉退潮交织,传递出苍茫时空中的渺远感怀。
通过《题金陵渡》与《瓜洲闻晓角》,我们可见张祜其人:一位清醒的旁观者、一位敏感的感伤诗人,更是一位于孤寂中寻觅美与宁静的生活美学家。他的态度并非激昂奋发,也非消沉避世,而是在漂泊中保持审美敏感,在孤愁中修炼超然心境。
张祜一生仕途失意,以布衣终老,可谓典型的唐代漂泊文人。但他并未沉溺于愤懑或绝望,而是将生命的憾恨与孤独,转化为对自然万物和内心世界的深度观照。羁旅孤寂、时光流逝、山河阻隔——这些生命中共通的“负面”体验,经他的诗笔提炼,皆升华为永恒的美。
他所传递的态度,跨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辉:生活的品质,并非全然由外在境遇决定,更取决于内心观照世界的方式。即便身处孤途,只要持守一颗敏感、宁静而超然的心,仍能于寒星、残角、斜月、渔火之中,捕捉到生命深处的诗意与寂静。
这是一种在失意中守护精神丰盈的力量,也是一种源远流长、充满东方智慧的生命哲学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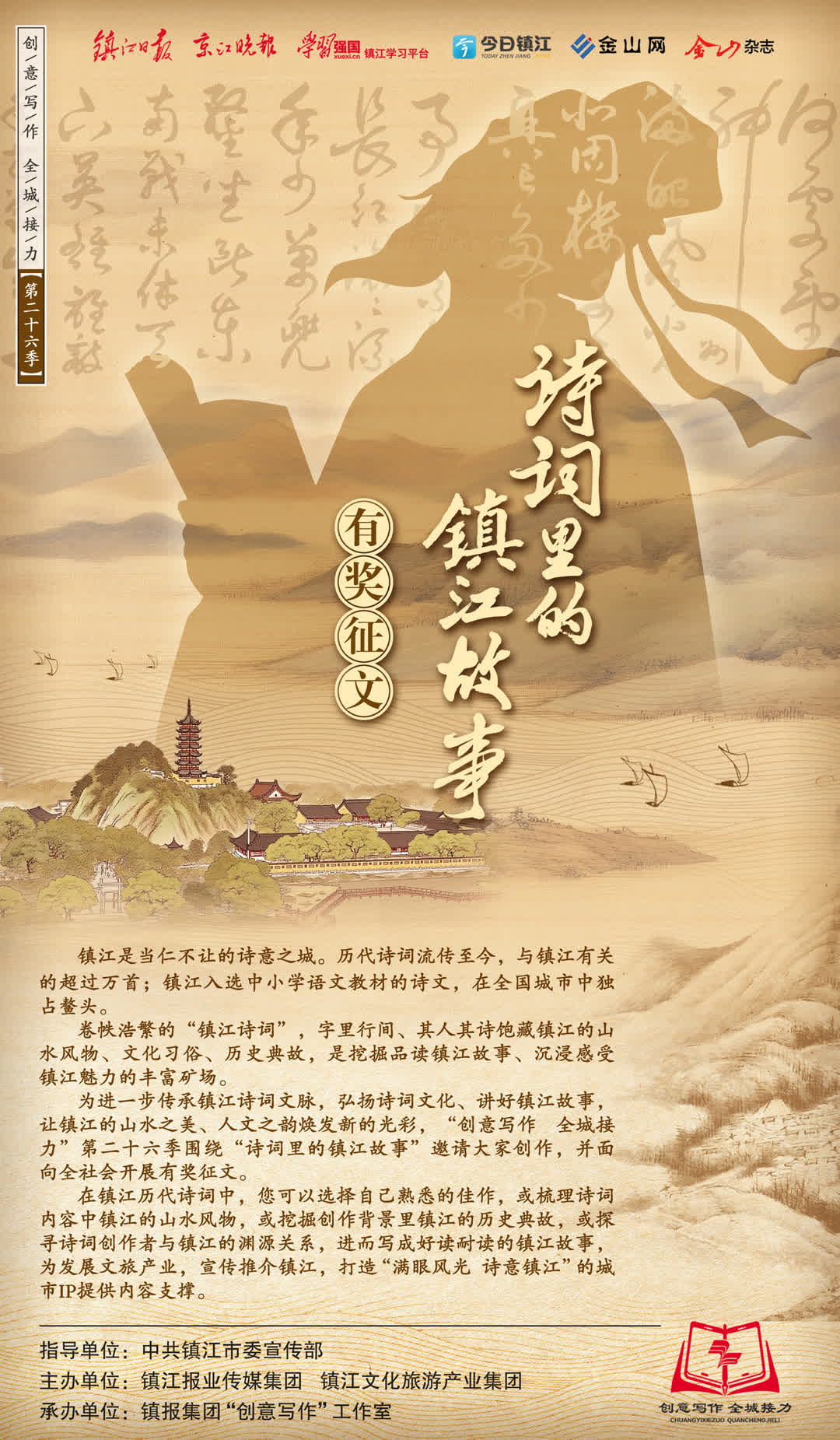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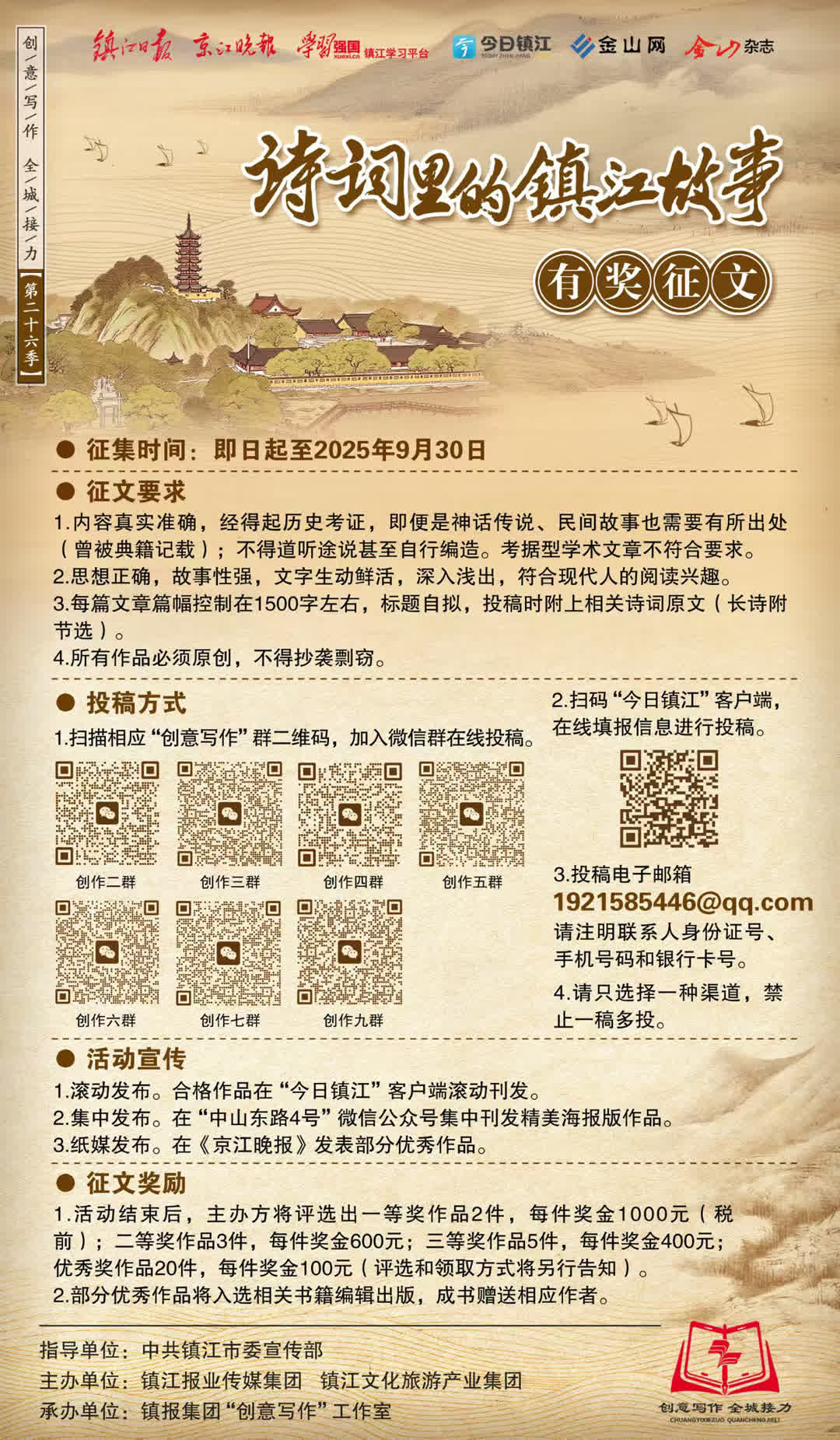
文字整理:吴韵晗
海报设计:谢志斌
编辑:毛蕴劼 校对:朱超 审核:徐毅 值班:许益明

